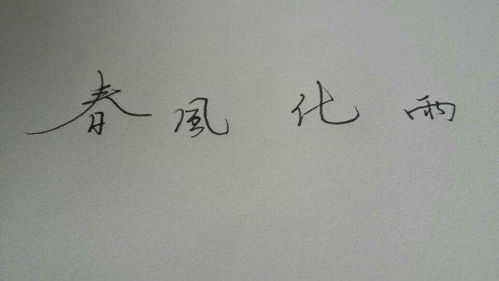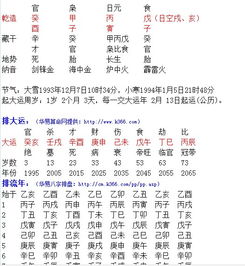劉悅笛 :“占卜” 之感性 理性到德性
從“占卜感性”“占卜理性”到“占卜德性”
文 / 劉悅笛關於《周易》與孔子的關聯,經學時代似有定論,民國之後又新見迭出。2018年以“天人合一”為主題的中印思想對話國際論壇開幕後留墨寶的過程中,致力於“易學本體論”建構的成中英寫了上聯的四個字——“知《易》行《易》”,然後就執筆停在半空,問筆者下聯該如何來對,筆者當場確無靈感未能及時應答,返家後腦海里卻突現下聯——“欲仁至仁”!
的的確確,古人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乃是知行合一的,這要追溯到遠古的占筮傳統那裡。關於易學史上的“兩派六宗”及其演變,《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說:“《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佔,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就象數派而言,漢初易學所講的象數尚與古法接近,焦贛、京房等人的象數易則大講天人感應、占驗徵兆。到了北宋的陳摶、邵雍那裡,象數易學得以再度興起,他們憑藉自己開創的河圖洛書、先天易學來探究天地宇宙的奧祕,於是《周易》不再貼近民用。就義理派而言,魏人王弼徹底罷廢了此前兩漢象數易學的思路,而用老莊思想解《易》,北宋的胡瑗、程頤則借《周易》來闡明儒家思想,南宋的李光、楊萬里又援史入《易》。表面上看,象數派更接近於“用”派,義理派更接近於“知”派,但無論兩派還是六宗,其實都是知行合體,只是偏重不同而已,因為中國思想始終貫穿著一種即知即行的“實用理性”。同時,筆者認為還有一種即覺即感的“實用感性”參與其中。
孔子更是一位以知貫行者,所謂“欲仁至仁”,顯然來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爾》),仁之道不遠人也。從“知《易》行《易》”到“欲仁至仁”,大概可以區分《周易》智慧與孔子思想之別,但這只是個非常粗淺的大致說法。晚年好《易》的夫子,究竟如何理解《易》與仁的關係?本文試圖從“巫史傳統”的角度出發來重釋《周易》與孔子的關聯,進而發現《周易》對於中國人的“情理結構”之歷史建構的深層影響。
一、從漢學家所謂“占卜理性”談起
《周易》體現了一種華夏遠古的“占卜理性”,“占卜理性”的獨特說法來自法國漢學家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他從思想發源的角度來看待中西文化及文字差異:“中西文化間有著深度的不同,兩者尤因表意文字與字母文字相去甚遠而相異,其對立之源在於,中國一方,思想最初以一種極為講究的占卜方程式為導向,希臘-拉丁與猶太-基督教一方,思想最初以宗教信仰為導向。”①這裡所說的“占卜方程式”是西化的說法,但占卜被“程式化”的確有賴於中國人對理性力量的使用,由此,汪德邁提出了中國獨具的“占卜理性”概念。
甲骨占卜代表了一種重要的歷史轉折,它標誌著“初始的神靈思想”轉向以宇宙某個代表物“占卜為依據的理性思想”,這一轉變在兩方面乃是決定性的:“首先,在信仰上,龜佔把占卜從通過祭祀乞知神靈善凶的初始參照中分離出來……這正是中國占卜理性與通往神學之道分叉而走向陰陽五行學的轉折點。其次是在技術製作流程上,龜甲占卜法在方法上具有實驗性……占卜師們成為完善這一投射的專家,並將構成此投射的兆文程式化,使之成為幾乎是科學性的占卜。”(《占卜與表意》,第15-16頁)顯然,漢學家對於遠古中國的“實用理性”給予了過於科學化的闡釋,科學占卜並不存在,但是占卜裡所蘊含的科學萌芽與理性內蘊卻是實存的。其實,這種轉折的更深層的根源在於“巫史傳統”,這種傳統帶來的天人溝通才是中國遠古思想沒有走向神學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汪德邁所見的通向了實乃後發的陰陽五行學。汪德邁判斷的缺憾在於,既把中國化的思想根源與後來思想之勾連說得太晚,又把西方式的科學思想在中國說得太早。
究竟何為“占卜理性”?這恰恰關乎中國占卜學精神本身的崛起:“占卜理性的精神,它把現象世界的無窮偶合化為幾種格式化的、付諸計算的知性。這一精簡過程是抽象化的過程:‘卜’的型別化是對無數未設定的卜兆的抽象。而這裡,史前泛中華文明在該階段所獨有的努力,其特徵是,在文字產生之前,抽象化是通過技術機制化進行的。卜兆的標準化工作是理性化的媒介。這是一種先進的、足以為中國表意文字之創造開闢道路的理性。”(《占卜與表意》,第15-16頁)按照這位漢學家的解讀,中國文字在占卜工具化製作的過程中才產生:“文字的創造自然是占卜官的事,占卜官從事造字,完全在占卜理性這線條上,占卜理性是中國占卜學有所演進的基礎。”(《占卜與表意》,第49頁)我基本贊同此種“占卜理性”的構想,並以之為華夏占卜學的思維根基之一,但是不贊同這種中國文字晚起說。
漢字是否與占卜共生,或者漢字是否源自占卜,是個歷史問題。汪德邁的獨斷也在這裡,他反對下面這樣一種架設:“存在一種早於甲骨文的文字,沒有它,就無法解釋甲骨文的絕倫精密。”(《占卜與表意》,第62-63頁)占卜官的確會造新字,但在他們擴充套件文字之前,也許從“結繩記事”時代開始,漢字就孕育了,只是後來在占卜當中得以廣泛運用與極大擴充而已。但是,這種中國文化的抽象化之理性過程,的確是占卜活動帶來的(文字是人類理性的顯現而理性並不僅以文字為顯現),這一方面源自技術操作上的“實用理性”,由此理性才成為踐行的;另一方面則是將萬物抽象為符碼的抽象理性使然,由此理性才成為知性。
然而,漢學家的另一個判斷卻可能是接近史實的,那就是認定甲骨占卜與八卦原型之間具有更深層的關聯。這種關聯最早的發掘者是古文字學家張政烺,他在1977年吉林大學古文字討論會上就富有洞見地指出,不僅“銅器銘文中三個數字的是單卦(八卦)”,而且陝西岐山縣出土的卜龜當中,“周原卜甲六個數字是重卦(六十四卦),周易中老陰少陰都是陰,老陽少陽都是陽,數字雖繁,只是陰陽二爻”。而且,分析29個不同器物殘片上的32條數字格式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數字格式只能從蓍草占卜的雛形意義上來解釋,他還對這種筮法加以初步蠡測並認定占卜已經從國之大事延伸到日常生活當中了。②這種研究已顯露出從遠古占卜到《周易》八卦的歷史綿延性,《周易》是“占卜理性”的某種主流結晶。關於與乾、坤卦名有關的商周古文字的近期研究也證明《周易》的“爻辭、卦辭與甲骨文一樣是記載占卜成果的文字。卜骨與卜筮是不同的占卜方法,但是無論什麼卜法,占卜語言的特點都接近……甲骨文和《易》都在深層系統地表達古人對天地與人生規律的認識”③。過去那種將八卦原型與甲骨占卜法視為兩種相互獨立的占卜法,認定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關聯的看法需要重新審視,二者其實有著更深層的歷史關聯。
汪德邁將這種理性逐步成熟的歷史聯通過程描述為:“該理性運作首先完成了從原始骨佔到龜卜佔的轉變,進而是龜璺規範成卜,之後從卜形變數到筮佔數字,最後應該是從原數字卦成為易經之重卦。”(《占卜與表意》,第63頁)這位漢學家同時關注占卜與表意兩種理性的相互推動與逐步成熟:“甲骨文字之所以突然如此精密,僅乃因為占卜科學的水平高階,表意文字的發明是其發展的頂峰。同樣,卜片上出現數卦原型,不能將之簡單地解釋為伏羲深化中的原始筮佔,在殷朝時代突兀地出現,它的出現是占卜科學理性向數字理性的過渡的標誌。”(《占卜與表意》,第64-65頁)由此,數卦原型向“易經數卦原型”的轉變,就被視為是在“理性化運作”中延續完成的,這個判定是很準確的。
從人類智慧發展的高度來看,這是從“象徵符號體系”到“數字符號體系”的飛躍,一般認為這構成了一種“數字理性”,但是漢學家認為:“隨著蓍佔,人們從占卜學的形式(規以卜兆形)類比思辨進入抽象程度更高的數字思辨,思考奇偶數之分的營數。初看上去,這是通過對龜卜術的形態——邏輯理性的超越、達到的數學理性而完成。而事實絕非如此。取自《易經》的數卦法與龜卜佔用的是同一種形態——邏輯。”(《占卜與表意》,第59-60頁)的確,這揭示出龜卜佔與數卦法的歷史關聯,但是向數字符號的跨越並沒有達到徹底抽象化的數字理性高度,其中始終融匯了感性的形式與內蘊,這就涉及“占卜理性”之外中國古人所具有的另一大智慧源泉——“占卜感性”。
二、與“占卜理性”融會貫通的“占卜感性”
從《周易》智慧的思想深層出發,筆者認為,僅僅關注中國人的“占卜理性”是不夠的,與理性相對而出並與之融會貫通的,還應有一種“占卜感性”,而且“占卜感性”無論在邏輯上還是歷史上都是居於“占卜理性”之先的。中國文明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占卜感性”與“占卜理性”的交融統一,儘管我們在做出如此劃分之時,感性與理性已然被割裂開來,但是中國智慧恰恰達到了二者的陽陰互動與動態平衡。
《周易》所講求的“感通”,亦即“感而遂通”,就是中國人“占卜感性”的深度顯現。當然,這種感通必先有《易》之“象”本身的感性顯現作為客體物件,但是更關鍵的還在於人作為主體如何與之感與通。因為所謂“‘通’就是人與易文字互動滲透、融為一體,文字內涵的天地萬物之道,與人性及其原有的觀念吻合,而顯現於人的內心世界之中。換言之,人的內心世界思顯現的正是文字中的那個‘顯諸仁、藏諸用’的道,人心與文字互顯互詮”。④顯然,這是一種從現代闡釋學視角出發的闡發,但闡釋學更偏重於思想的理性闡釋,而《易》之通卻不是“思通”,是“感通”,這個感就是感性之“感”。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易·繫辭上》)《周易》本身既是沒有“思”的,所以無法與之“思通”,也是無有“行”的,所以就需要人經過“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周易·繫辭上》)的理性與感**織的活動,如此才能“通其變”從而成就天地之文。因為君子既有“為”也有“行”,他們在筮佔過程當中溝通天人,從而達到“其受命也如響”的通達之境。當然,這種通達並不是人與天的“直通”,還需要以蓍草這樣的“神物”為中介,“極其數”,定卦象,“遂通天下之故”,這就不是“占卜理性”所能達到的了,“占卜感性”在其中同樣發揮著核心的功能。
經由《周易》而生髮的這種天人“感通”,不僅要感而“通”之,而且要通而入“神”,這就指向了更高的神“通”境界。“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周易·繫辭上》)感通進入“神”境,就是人之神與天之神內外通之,“往來不窮謂之通”。這種神而“無方”所獨具的能動性,大概不是“占卜理性”所能規制與束縛的,而是具有了某種感性化的自由性質與維度。由此,“占卜感性”就訴諸人與《易》的交感,它可以知“幾”入神,在把握“成天下之務”的幾微基礎上,進入一種“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通“神”境界。
我們可以從外在天地與人自身兩方面來看待“神”:一方面,古人“神明”的本義乃指“天與地之間的交通過程,進而衍化為天地之間最重要的媒介,成為天地之間的氣化主宰者,成為造物‘生機’之源”⑤。在易學思想裡,神明與陰陽也有“德”與“體”之分:“神明系天地分合其‘德’之過程,也是未分定各‘體’的狀態;而陰陽兩儀,則分合天地之現象與形體……‘神明’可以說是一種‘宇宙一體’的狀態。”⑥但另一方面,感通的主體仍是人,“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周易·繫辭上》),聖人更能“見天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周易·繫辭上》),由此方能夠“繼志述事”,從萬物生生見天地之“志”,從陰陽妙合見天地之“事”。所以說,“易道寂感之神”,“非人格神之神,亦非從氣而言的神,而是從天道易體神感神應妙運生生而言之”。⑦於是,所通之“神”便超越了主客,從而達到一種“妙萬物”而“窮神知化”的美境。這種美化的境界恰恰是由“占卜感性”而非“占卜理性”生髮出來的,因為中國審美追求的最高境界恰是這種妙合之化的“神化境界”。
實際上,在用《易》中得以凸顯的“占卜感性”與“占卜理性”皆來自更為久遠的“巫史傳統”,這一傳統形成了中國人的“情理結構”。或者說,中國人“情理合一”的文明根源,其實在於巫史傳統的歷史塑造。汪德邁也意識到了這個歷史性根源:“在占卜成為科學性占卜學,宗教成為禮儀體制的同時,薩滿古老的舞蹈也轉變成一種《詩經》的頌舞禮儀,該禮儀從其迷人的跳神原型中繼承了一種通感力,禮制開發了它,同樣,文言從其占卜原型繼承了一種闡釋力。”(《占卜與表意》,第40頁)這就是將“宗教禮儀化”轉化成為“完備系統的文化機制”。這個歷史轉化過程,我曾歸納為巫的理性化、政治化與文明化的過程⑧。其中所說的“通感力”就是巫通天地的“內通”,它更關乎“占卜感性”而非“占卜理性”。
知《易》行《易》要得以實現,那麼,對《易》的知就不能只是“認知”,更要有“感知”,前者是(知“道”的)“占卜理性”,後者是(“感”通的)“占卜感性”。而且,這個“占卜感性”趨成了《易》之美學,因為在西方原本的語境當中,“美學”(aesthetics)的本意就是“感性學”。以往的《周易》美學研究深受宗白華的影響而更多從“象”的角度入手,但其實可以拓展開來,轉而從“占卜感性”直接入手。從更廣闊的思想高度觀之,這種“占卜感性”並不像“占卜理性”那般可以直接歸屬於中國人的“實用理性”,而應歸之於“實用感性”的歷史發展序列之內。
在“實用理性”與“實用感性”合一的大背景下,占卜的理性與感性的融會貫通跟夫子與巫史傳統的勾連有關:一方面,儒家思想有來自巫史的淵源,這一點筆者深受李澤厚相關思想的啟示。當然他的“由巫到禮,釋禮歸仁”還注重以“禮”為中介⑨。但另一方面,孔子開始走出了巫史,從而與“巫史傳統”形成了一種不即不離的關聯。這就是孔子“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的深意所在,它形成了一種當今學人所說的“如在主義”:它“既非有神論,亦非無神論,更不是懷疑論或者不可知論。它關注的焦點不在於神是否真的存在,因而也不是對神的信仰,而是人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方式去參加祭典、去進行精神性的活動”⑩。由是觀之,如在,不是不在,而是“如”其所在,實在卻“如在”。那麼,孔子是如何實現這種“如在主義”的呢?這便關乎孔子與《易》的問題。
三、脫穎的“占卜德性”與“幽贊—明數—達德”架構
孔子與巫術傳統到底是什麼關係?據馬王堆帛書《周易》的《要》篇記載,夫子本人明確表示:
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11)
我們由此切入《易》孔關係,從巫史傳統的角度審視其關聯。如果帛書《要》篇能在一定意義上顯露出孔子本意的話,那就說明,孔子對《易》的態度前後有所變化。“孔子在晚年以前視《易》卜筮之書,認為它是和德行、智謀相悖的,其不好的態度十分明顯……只有在孔子‘老而好《易》’,認為‘《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易》剛者知其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忘(妄),漸人為而去(詐)’,甘冒‘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風險時,才有可能發出‘學《易》可以無大過’的感嘆,才能產生‘加我數年’的願望。”(12)
從早年不識《易》、不認同卜筮到晚間深知《易》、接納占筮,反映了夫子逐漸“成人”的過程。從理論上說,夫子對經典的認識是逐漸深化的,晚年反覆研讀《周易》之所思所得更接近於《易》的本質。從踐行上講,晚年孔子周遊列國而顛沛流離,對於命運無所把握時用《易》來測度未來,這也是符合情理的。“韋編三絕”的反覆玩味,甚至被《要》篇描述為“居則在席,行則在橐”般的熱衷,也使“老而好《易》”抑或“晚而喜《易》”(《史記·孔子世家》)的孔子形象得以呈現出來。
夫子的自我表白——“《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是孔子研《易》用《易》的核心要義。據張政烺的校注“言關於易學,我以祝卜為後,而以德義為先”(《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第167頁),這一先一後的順序,恰恰顯示出夫子的獨特易學觀:德先卜後,德在卜前。儘管孔子並不否定卜筮,但他“不安其用而樂其辭”,不僅拿《易》來佔“用”,而且以“辭”的內蘊為樂,於是進入到《周易》的思想深層。從“祝卜”到“德義”的轉化,正是孔子的“如在主義”。既不否定卜筮,又認為它在祝卜之後,並從《易》中“觀”到了德義,這其實是把巫道德化乃至文明化,上升到“德義”的道德層級,從而近於“仁”境。
《要》篇記載了弟子對孔子態度前後不一的質疑。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惪(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智)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早年教育弟子“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無德行的人才趨於神靈,“智謀遠者,卜筮之繁”,缺智謀的人才會頻繁地卜筮。夫子卻自認為這與晚年好《易》並不矛盾,事實上也是如此,德先卜後與德在卜前的晚年主張,與他早年“德行”在“神靈”之先、“智謀”在“卜筮”之前的立場是一致的。
“幽贊—明數—達德”是孔子把握《易》的內在邏輯的架構。“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通過知《易》而行《易》,夫子最終要達到的是“仁守”而“義行”。甚至可以將知與行拆開來說:“知《易》”要達乎“守仁”,“行《易》”則要達乎“行義”,如此,對《易》之知行也就達到了“仁義”。這個求仁得義的過程,筆者稱之為對“占卜德性”的尋求。向這種更高的“占卜德性”轉化,正是儒家得以超出“巫術傳統”的根本原因。
帛書《要》篇曰“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這一讚一數、一巫一史,恰將《易》與巫史傳統勾連起來。這個論述非常關鍵,因為它說明了夫子究竟如何延續了“巫史傳統”,又何以走出了“巫史傳統”,而且,巫傳統與史傳統也被分別加以處理。一般人會認為,巫之《易》主“幽贊”,史之《易》主“明數”,夫子之《易》主“達德”,似乎有著不同的知《易》與用《易》的方式。其實,巫傳統與史傳統並不能決然分殊,“史”作為一種歷史角色,其本意源於用動物甲骨占卜後在骨上著顏色的特定身份的人,他們曾是參與卜筮的記載者。巫人“幽贊”,張政烺的釋讀為“贊,解說。幽,深微”(《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第167頁),這種“贊”是感性顯現,但是在巫人的“解說”當中又有理性化的闡明。雖說巫人難達於數,然巫人用數卻史有記載,史者也在史上從於巫,巫與史難分,但二者都未能“達德”。孔子則讓“德”從巫史中脫胎出來,這是孔子解《易》的真正拓展之處。
從“幽贊”“明數”到“達德”,後世論者認定其發展邏輯是一種歷史的邏輯:“贊”之用作為《周易》的原初之用,是邏輯起點;經由與人較遠的“自然理性”,亦即“數”,歸結為與人德性直接相關的“人文理性”,亦即“德”。(13)這樣做的前提是,“贊”與“數”顯現的是天道,而“德”顯現的則是“人道”,同時意味著,從“贊”開始,先是達到“數”的自然理性,進而達到“德”的人文理性。然而問題在於,無論“贊”還是“數”都不只是先天的自然理性,“幽贊”的解說深微乃是人為的,而“明數”更是後天的理性抽象出來的,“數”實乃人類的“發明”而不是對自然的“發現”。況且,這種自然與人文理性的二分,尚未得見孔子於先天與後天、自然與人文之間本然融匯的狀態,也未看到自然與人文兩種理性當中都蘊含著感性的成分,中國人的智慧就在於感性與理性的平衡與統一。
筆者認為,從“幽贊”而“明數”,的確達到了“占卜理性”,而且是數理化的理性,同時亦以感性形式呈現。“幽贊”更多彰顯了古人的“占卜感性”,其中也包孕著理性成分。如此觀之,以“占卜感性”為主的“贊”走向以“占卜理性”為主的“數”的同時,也開始從“巫”中走了出來,因為巫在此已經被理性化了,而且被一定程度地數理化了,這就是從“巫”到“數理”的突破。儘管此“數”仍為筮佔所用,排列“數”的呈現方式仍包孕著感性組合的表象功能,但是數理化的傾向已不可逆轉。
進而,從“明數”到“達德”,就是達到了“占卜德性”,而這種德性當中包孕著占卜的感性與理性雙重成分,脫胎於二者又超越了二者。如此,“占卜德性”不僅從“巫”中而且從“史”中脫胎出來。占卜當中“史”的原本歷史角色不囿於“明數”而昇華為道德時,那就實現了從“史”到“倫理”的根本突破。這種道德昇華,既是從“天道”而來的,更實現了一種“人道”的突破,或者說,從“天道”貫通於“人道”,由“人道”實現了“天道”,中國人的天人智慧得以由此盡顯。
質言之,從《周易》到孔子有雙重突破:一方面是從“巫”到“數理”的突破,另一方面則是從“史”到“倫理”的突破,這是對“占卜感性”與“占卜理性”的雙重超越,也終成“占卜德性”的昇華。然而,數的“象化”與倫理的“感化”裡面又包孕了“占卜感性”,而占卜的感性與理性二者始終是合一的,從而構成了中國人原始的“情理結構”,這才是《周易》對華夏文明的深層巨大貢獻。
結語:從“以《易》求德”觀中國人的情理結構
本文聚焦的歷史問題是:易學智慧到底如何塑造了中國人的“情理結構”?或者說,中國人從古至今的“文化心理結構”受到了《周易》多廣抑或多深的影響?
夫子經由《周易》,穿越《周易》,又超越《周易》,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其最重要的超脫就在於“道德理性”的昇華,這也就是“由巫到仁”的歷史轉化。實際上,這種“化巫為仁”乃是歷史積澱的產物,需要從經驗到先驗的累積沉澱,仁始終沒有逃棄由“巫通”而來的與天地的溝通,始終是現實人們所要遵循的德之“道”。“巫”貫通天人,“史”延續古今,或者說,巫與史有差異,“巫”使得天人合一,“史”則讓歷史延續。(14)巫史傳統的“占卜感性”與“占卜理性”及其合一,恰為“占卜德性”的脫穎而出奠定了基礎,中國人的“情理結構”也由此而生,《周易》對於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的塑造確實功莫大焉。
我們再以占卜的感性、理性與德性的三維結構來反觀整個易學史的發展。在易學史上,“象數派”儘管凸顯符號化,卻更傾向於數字化的“占卜理性”,同時也注重以形式呈現的“占卜感性”;“義理派”則以道德化的“占卜理性”為主而以融情入理的“占卜感性”為輔。這從邵雍和程頤的釋《易》張力當中就可得見,但是象數與義理兩派到了宋代又皆重孔子所開創的“占卜德性”。“占卜感性”與“占卜理性”的統一,恰恰有賴“占卜德性”之整合。有趣的是,到朱熹那裡,似乎又在某種意義上回歸了《周易》側重卜筮性的維度,這是巫史傳統在易學發展史上不斷隱現的現象,說明巫史傳統始終未斷,但《易》在朱子那裡終究是服務於“聖人之道”的,也終歸於“占卜德性”。
如此觀之,孔子可以被視為“占卜德性”的創立者,他對“史巫之筮”採取“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的態度也就易於理解了,儘管對史之筮和巫之筮也有所向往,但用《易》卻大異其趣。《要》篇記載了孔子占筮的具體情況,弟子問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夫子答曰:“吾百佔而七十當。”需要強調的是,夫子是以“占卜德性”的立場對待占筮,明言“吾求其德而已”,這實際上是“以《易》求德”,因此未囿於巫史那種低階的感性和理性層面,而是由此生髮出對德性的更高追求。在這個意義上說,夫子與巫史同一途徑,所歸卻差之遠矣。
《要》篇所記“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進一步解釋了為何“祝巫卜筮其後乎”,夫子對於祝卜與巫筮的態度昭然若揭。“德行焉求福”,“焉”義為“乃”(《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第167頁),即行德就是求福。祭祀是為了求福,君子當然也求之,不過,以德行之,福自然也會來。可見,中國人較早提出了“德福一致”的問題,儘管現實中二者的統一往往不能達到牟宗三意義上的那種“圓善”高境(15)。行了“仁義”,就不必多用卜筮了,這其實就是夫子的“如在主義”。在對待巫史傳統上,夫子採取了一種“祭神如神在”的態度,這正是中國人“一個世界”的大智慧。儘管祈神敬神,卻並非徹底拜倒在神之下,人是頂天立地的,人得以“成人”是以“仁”為核心的道德理性使然。
總之,從知《易》行《易》而來的道德意識,並不是純然的倫理理性化,其中必然有道德的情感浸漬其中,這就是中國人的“情理結構”。道德之情與道德之理乃是合一的,發乎情而止乎禮,由此達到一種動態平衡,這種智慧在晚年孔子“以《易》求德”那裡就已經被開啟了。
註釋:
①[法]汪德邁著,金絲燕譯《中國思想的兩種理性:占卜與表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註書名簡稱“《占卜與表意》”與頁碼。
②張政烺《試釋周初書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卜》,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
③郭靜雲《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97-598頁。
④林忠軍《易學源流與現代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1頁。
⑤郭靜雲《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第624頁。
⑥郭靜雲《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第625頁。
⑦蔡仁厚《中國哲學史大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第61頁。
⑧劉悅笛《巫的理性化、政治化和文明化——中國文明起源的“巫史傳統”試探》,載《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⑨李澤厚《說巫史傳統》,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李澤厚《由巫到禮釋禮歸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⑩倪培民《儒學的精神性人文主義之模式:如在主義》,載《南國學術》2016年第3期。
(11)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59-160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註書名與頁碼。廖名春《帛書〈要〉釋文》,載《帛書〈周易〉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89頁。
(12)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151-152頁。
(13)呂相國《帛書〈易傳〉理性精神內在架構蠡測》,載《中州學刊》2013年第5期。
(14)李澤厚、劉悅笛《歷史、倫理與形而上學》,載《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1期。
(15)牟宗三《圓善論》,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0年。
熱門文章

七里香的風水禁忌,家庭種養七里香有什麼好處七里香的風水作用與影響
家庭種養七里香有什麼好處 七里香的風水作用與影響植物都是有靈性的,植物含五星,植物之間以及萬物之間 ...